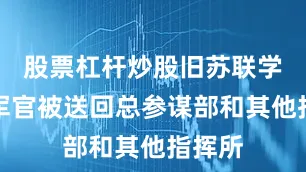赫鲁晓夫的十年:从矿井少年到古巴海风里的冒险者
春天的库尔斯克省,地面还带着冬雪化开的泥水。1894年的一个清晨,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·赫鲁晓夫出生在这里——一个农民家的木屋里,窗子缝隙里灌进冷风。他父亲是个季节工,有时去顿巴斯挖煤,有时帮人修犁头。母亲会在炉边给孩子们烤黑麦饼,那味道后来成了他记忆深处的乡愁。
十五岁那年,他跟着父亲去了顿巴斯,在矿井当机械学徒。矿灯昏黄、煤尘呛鼻,他第一次见到那些被石块砸断手指的老工人,还听他们用粗话骂沙皇和厂主。据说,就是在那里,一个乌克兰籍技师塞给他一本破旧的小册子——列宁写的小册子,纸页已经卷角。他没读几行,就觉得心口发热,好像找到了能解释自己命运的话。

1918年,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。当时正是内战最乱的时候,他被派去做政治宣传工作。有一次在火车站台上演讲,被白军冲散,人群中有人喊:“那个矮个子的红党小伙跑快点!”多年后他回忆,这种场面让他明白,“嘴上的仗”有时候比枪还要危险。
时间跳到1930年代末。在莫斯科地铁建设现场,年轻干部赫鲁晓夫穿着沾满灰浆的皮大衣四处巡视。他喜欢直接下坑道看施工,不怕弄脏鞋。据一位当年的工程师回忆:“书记走过来,会拍拍你肩膀问家里情况。”这种接地气,让他的名字很快传遍了莫斯科,也为他升任乌共第一书记铺路。当时乌克兰刚经历饥荒与肃反,人心惶惶,而他的作风显得格外不同——虽然也执行高压政策,但偶尔会放一些缓气儿,比如批准某些学校恢复教学活动,这在当时算是“破例”。

战争来了。1942年的伏尔加河畔,他作为政委参与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。有士兵回忆,在最冷的一天,他们窝在半塌的房子里取暖,赫鲁晓夫蹲下来,从怀里掏出一小瓶烈酒分给大家,说:“喝一口,我们还能撑。”这样的细节,很少出现在官方档案,却留在人们记忆中很久。
1953年9月3日,他坐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。这一年夏天,在权力斗争中击败贝利亚,是个转折点。但真正让世界震惊的是三年后的二十大秘密报告——那份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》的长篇批判,把“大清洗”的血腥细节摆上桌面。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后来私下说,当听到“滥杀无辜”几个字的时候,会场空气像凝固了一样,有代表低声咳嗽,还有人低头抹眼睛。但这场揭露并没有彻底改变体制,只是在冰封的大地裂开了一条缝隙,让一些阳光照进来,又迅速被云遮住,比如匈牙利事件就是那片阴影之一。

农业,是他的执念。他推行玉米运动的时候,据说曾拿着玉米棒对农学家拍胸脯保证:“它能养活全国。”哈萨克草原因此多了数千万公顷新垦土地,一开始产量确实猛增,可几年后土壤板结、风蚀严重,一阵干旱就把收成打回原形。有村民调侃,“书记送来的不是金棒,而是空杆”。1963年的粮食进口,对自诩农业强国的苏联是丢脸又不得不做的事。
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,更像是一盘高赌注扑克局。在黑海边度假的一天晚上,据随行翻译讲,他突然摊开地图,用铅笔圈住古巴,说要在那里放几颗“大烟囱”(核导弹)。动机很简单:美国人在土耳其架起导弹对准我们,我们也该让他们睡不安稳。然而事情发展得太快,美军封锁海域,全世界屏住呼吸等消息。从莫斯科传出的电报语气越来越急,到最后只能撤走换取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。这件事国内外解读不同,但党内很多人觉得,这是一次暴露短板又没捞到好处的冒险行为。“赌徒”,这个词从此悄悄贴到了他的背上。

权力滑落往往发生得猝不及防。据秘书后来透露,1964年10月的一次假期归来前夕,就有人劝他别急着返京,因为中央正在酝酿“调整领导班子”。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动作干净利落,以健康为由请他退下。从此,这位曾经拍桌子的领袖搬进郊区一栋两层小楼,看花园里的苹果树发芽、结果,再掉落腐烂。他开始口述自己的经历,由儿媳偷偷带出去,经西方出版,那本书至今还有收藏者以高价求购,因为里面夹杂了不少私人情绪和内部八卦,比如某次宴会上谁喝醉摔杯之类的小插曲,都写得生动刻薄。
1971年的初秋,一个普通周六上午,据邻居老太太讲,她看到院门虚掩,没有平常早晨修剪玫瑰花枝条的人影。不久便传出噩耗——心脏病夺去了这位前领导人的生命,没有国葬,也没有万人送别,只剩下一段复杂而摇摆不定的历史评价。

我去年路过库尔斯克附近一个村庄,小卖部老板娘提起这个同乡人物,说她奶奶年轻时候见过一次,“个头矮矮胖胖,不爱戴帽,总眯眼笑”,然后递给我一杯温啤酒。我想起这一幕,总觉得,比任何厚重史书都更贴近那个真实的人。
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,仅供学习交流,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
百胜证券,配资网上配资,华泰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